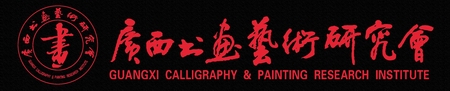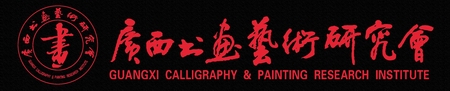中国画理法基础研究
中国画理法基础研究
——中国画的法则与笔墨问题
广西书画艺术研究会 园稻林
中国画是我国劳动人民和艺术家们留给现代中国的一份优秀文化遗产,它不仅艺术风格别致,而且艺术成就也极高。中国画从宋代趋于成熟至今的一千多年间,名家大师辈出,为中国画的技法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从前人留下的精湛艺术珍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深的理论著述诸方面的成就来看,都有待我们后人很好地研究,继承和发扬,并使它从一个艺术高峰发展到另一个艺术高峰。以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宝库,让它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彩。
一
下面谨就中国画的实践、认识、构思、构图方面的法则作一些阐述和探讨。
(一)主观、客观相忘的法则
绘画中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任何创造性劳动,包括艺术创造在内,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而实现的。即使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原始绘画作品也是如此,不过古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仍然处在摸索阶段还不能自觉把握主、客观的关系来进行绘画创作。从晋代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和“迁想妙得”开始探索主、客观的关系至隋代的姚最提出“心师造化”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关系以后,直到中唐张璪提出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才使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结合起来了。从此,后人在以大自然为师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者的主观艺术创造性,进行了广泛又深入的实践,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作者在表现景物神态的同时,如何表现作者的精神气质,并达到“物我相忘”的高度。前人的经验表明,要使中国画达到高妙的境界,必须使主、客关系统一起来,参悟相忘。传统画论中的“似与不似”,“绝似与绝不似”就是主观、客观相忘原则的要求。所谓“物我相忘”的意思,就是要求灵活地、成熟地处理主、客观的矛盾关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融相化。既“写自然之性,亦写吾人之心”(黄宾虹语),达到“造化入画,画夺造化”(黄宾虹语),“失于自然,而后神也”(董其昌语)的目的。
(二)理性、感性相应法则
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是开始某些感性认识,然后在理性认识的指导下集中、加工、提炼创作出艺术品来。这是一个艺术创作过程,也是艺术认识的原则之一。理性认识的内容应包括画理、画法及审美要求。只有掌握中国绘画的理法要求,才能更好地指导自己的写生、临摹和创作。感性认识是艺术家在体验生活时的灵性冲动。表现在绘画方面的:形象的联想、景物的浮现,难忘的情景、特殊的场面,美妙的对象等都可以引起意境的联想,某一素材可以引起画面构图设计。在绘画的实践过程中,应不断使感性认识得到丰富和使理性认识得到深化。在写生、临摹、观察的时候,不但要丰富感性认识,同时要善于通过感性认识的概括,认识事物的规律性,上升为理性认识。在创作构思的时候,不但要运用理性认识的指导,同时要使认识仓库中的感性积累,分门别类的涌现出来,以提供创作的资料。
应该加强绘画理法的学习,熟悉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性,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能使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较好地相结合,不断提高绘画创作的艺术能力。
(三)抽象、具象相化法则
抽象(又称类相)与具象,也指共性与个性而言。中国绘画中的抽象就是概括形象,具象就是特性形象。这种特性形象和概括形象有生机地组合,形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特殊境界。在自然界,景物千差万别的,但也有大同小异与小同大异之分。画家们就是要在千差万别中去寻找美的因素和表现手法。那些个性特殊的景物,被画家们摄取过来,成了画中的具象。例如松树、柳树、竹子、梧桐树。而那些大同小异的景物,被画家们加以概括了,成了画中的抽象(类相)。例如:胡椒点代表小叶树,大墨点代表浓密的丛树等。这原因是具象能给人具体感觉,对象的风姿生态使人们获得具体形象,抽象能给人总体感觉,对象的共同之处,给人一种概括印象。这种具体形象、概括印象的重复、返复、交错是人们认识外界的习惯。画家为了适应人们这种习惯,往往以具象为主景来组织画面,抽象(类相)则为之衬托在删去许多次要的具体形象后代之以抽象印象,不仅能使人们的注意集中在主要具体形象上,得到明确感觉,同时,抽象又能使人产生模糊的联想。这样相衬相托,主体形象给人的感受更深了。例如:一幅山水画中,全是一种树形会显得单调,主体又不突出;如果各种各样的具体树形堆集布满画面,又显得繁杂。只有类相、具相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才会使画面显得丰富多彩。选择具象要千锤百炼,个性突出,或阿娜风采,或挺拔英俊,抽象也要活泼多姿,爽朗传神。社会上有一种所谓“水墨大写意”,只是大笔一挥,涂涂抹抹,虽然也算是有一点“抽象”,但是缺乏鲜明的具体形象,只剩下一片模糊,景物的美和形都被抽掉了,并不太符合抽象、具象相生的原则。
(四)阴阳、黑白相生法则
没有阴阳,不成气候,没有黑白,不成画面;没有阴阳,无有生气,没有黑白,无处回旋。从大自然取象而构成画面,必须阴阳黑白相生。使观者感到画中有呼吸,有活动空间。可望、可思、可游、可居。所谓阴阳,一般系指景物的明暗、内外、背向、刚柔组织构成而言。具体所指是下为阴、上为阳,内为阴、外为阳,背为阴、前为阳,暗为阴、明为阳,凹为阴、凸为阳,柔为阴、刚为阳。还有以右为阴、左为阳,小为阴、大为阳,后为阴、前为阳之说。不过不要同玄理阴阳之说混为一谈。画中之阴阳主要体现为画面的黑白问题。这是个技法问题,也是一个理法问题。黑白问题,无处不在,知白守黑则阴阳相生了。在色彩学中,黑与白是对比关系,中间是灰,由于水与中国墨的特殊功能与作用,从黑到白表现了中国画墨色的整个“色阶”,它不需要色彩也能组成景物与画面,既能表现春夏秋冬,风晴雨露;也能表现喜怒哀乐与人生变化。西方画家不承认黑、白是色彩,而在中国水墨画里竟是一种主要形式,主要原则,主要技法和主要理论问题。一般人对黑白问题的理解是:有墨即黑,留空为白,或者施粉叫白。而画家作画时的要义为“知白守黑”。所以,画家应该明“白”,白不等于白色,白色也不能替代“白”。例如:画面没有表现某种内容的空处,可以叫做“空白”。表现一定内容和空间而留下的白,应叫“实白”,如天空、云水、雾气之属。山石屋宇之阳面留白,可谓之“光白”。画面需要而留出之空处,可以叫“意白”,于景物周边留下的空隔处,可以叫做“衬白”。明白了空白、实白、光白、意白、衬白的种种用意之后,作画时处理黑白问题才能如鱼得水,灵活自由了。黑白问题是形式问题,可以是抽象,也可以是具象。整体为具象时,局部即为抽象,宏观为抽象时,微观即为具象;相似为具象,不似即抽象,同时,必须使之融汇到画家的创作中去。当其表现景物形象时,为实;不表现任何内容时,为虚。黑中太实则易板、易刻、易死;白中太虚则乏气、乏情、乏味。务需做到抽象具象,互隐互变,相显相扶。力求虚中求实,实中求虚,才能黑白相应,虚实相生。黑白问题是技巧问题,也是创意问题,画家的创作激情,不只是灵感的闪光,也应该是思维的“灵感”。激情是沸点,浮在上面。理性则是落点,沉在下面,处在创作境况中的作(画)家。既是兴奋的,也应该是冷静的。他的创作情绪既浮在沸点,也沉在落点。这种反差越大越好,而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的缝隙,则越小越好。
(五)疏密、虚实相衬法则
大自然变化万千,景观景物皆可入画。但是,画中的“自然”,不是造化的自然。人们说的江山如画,正是指江山不如画。“画”是画家在写生与创作实践中,经过一番艺术构思“取舍”而成的艺术自然。所谓疏密、虚实问题,指的即是画面的构图、布局和虚实衬托处理方法。画中疏密问题古论很多。要求的是“疏中有密,密中有疏”,疏密相间、相衬、相托,而且是“疏中疏”则“疏可跑马”;“密中密”可“密不通风”。这些,从我们前人的佳作中可窥其奥妙。一般来说,无景为虚、有景为实,稀疏为虚、密迫为实,衬景为虚、主景为实,简略为虚、繁复为实,远处为虚、近处为实。从笔墨运用来说:无墨谓虚,有墨谓实,谈泊谓虚、浓重谓实,迷濛谓虚、清晰谓实,勾线谓虚、皴探谓实,间断谓虚,连接谓实。以画幅布局来说:空白谓虚、墨黑谓实,边沿谓虚、中心谓实,晦涩谓虚、明朗谓实。但是,仍需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处不是空虚,还得有景,密处仍须有立锥之地,切不可使人感到窒息”(黄宾虹语)。画中虚实,以“虚”最难处理。实处有景,虚处亦应有景。虚中有大虚、小虚,大虚最难处理。天、水、云、雾为大虚,皆可留白,全白又显得太空虚,需要虚中有实。山石树木也有阴阳、明暗可以留白,是为小虚。能阴阳相生,疏密相间,虚实相得,则绘事乃成。
二
笔墨问题是中国画的中心问题,也是中国画独特风格的基础。由于笔、墨、纸的特殊功能,运用方便自如,表现五花八门,效果千奇百“怪”,要求登峰造极。因此,笔墨问题就成为中国画作者必须着力解决问题之一。笔墨的使用是技法问题,笔墨的表现功用是理法问题。笔与墨的关系,则是共性的问题,非笔不能运墨,非墨无以见笔:墨自笔出,笔由墨显。相离究其理,相依以为用。各自变化,相辅相成,相化相生。
(一)笔墨的功用
所谓用笔,可分二说。一是如何使笔与力相结合,造型、造境这是用笔的技法问题;二是笔力与感情相融合,出神入韵,则是用笔的理法问题,二者兼备,或生死刚正,或婀娜多姿,骨架立矣。所谓用墨,也分为二。一是如何用墨色去表现景物的阴阳背向,完备肌肤,这是用墨的技法问题:二是如何以各种墨法去表现、衬托不同的画情、画意,是用墨的理法问题。技法用墨要求是掌握各种墨色之相互渗用;理法用墨则是要追求画面干裂秋风,润含春雨,元气淋漓的意境效果。中国画以笔线为支架,故以线为骨,叫做骨线。骨线表达某种感情和意义,则谓之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唐.张彦远语)。感情立意是丰富多样的,用笔也当然是丰富多样的。古人常说的“绵里针”、“屋漏痕”、“折钗股”、“如锥画沙”、“如虫蚀木”等,就是用笔的多种形象的表述和要求。中国画以墨取韵,“能浓淡得体、黑白相用、干湿相成,则百彩骈臻,虽无色,胜于青、兰、紫。”唐以前“均以浓墨线作轮廓……自王维始用渲淡,王洽始用泼墨,项(容)、张(璪)、董 (源)、巨(然)、二米(米元章父子)继之,发挥光大,而用墨之法,渐臻赅备。是后波涛漫演,壮阔无垠,成为东方绘画之特点,至可宝贵”(潘天寿语)。关于用笔、用墨的要领,大涤子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其论点是:“笔与墨合,是为絪缊,絪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得笔墨之会,解絪缊之分,作辟混沌手。画于山则灵,画于水则活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传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潘天寿论曰:“湿笔取韵,枯笔取气。然而枯中不是无韵,湿中不是无气,故尤须注意于枯中之韵,湿中之气。知乎此,即得笔墨之道矣”。笔墨要自然天成。依景物运用笔墨,依意象运用笔墨,更应该综合运用笔墨。熟悉各种皴法,描法和笔法、墨法。笔酣墨饱或笔瘦墨清,都应明乎其要领,或相互渗用,并使之得体。笔迹、墨痕要相化相宜,显而不露、含而不糊。笔路墨路要相就相让,又断又连,又隐又现。
有关中国画笔墨问题的名词述语,历来都是丰富别致而内含又是色彩缤纷的。要对它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作为当代有志趣的中国画画家,对中国画的笔墨问题不花点时间费点力气对其作出一定研究和感知,就很难称得上是合格的中国画画家了。
(二)笔墨种种(主要名词、述语的区分)
关于中国画笔墨的运用应该是变幻多彩永无止境的。所以,中国画的笔墨问题就成了古今以来画家和理论家议论不休的核心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也很难把中国画的笔墨问题撰述得十分清楚。因此,笔墨问题才是我们中国画画家必须长期研究的中心问题。在这里只就中国画画家历来就笔墨问题的种种论述中的称谓、名词,分别其含义与作用概述如下:
以运笔分为:落(起)笔、收笔、连笔、断笔、折(挫)笔、顿笔、长笔、短笔、飞笔。
以笔迹分为:方笔、圆笔、拙(稚)笔、凝笔、渗笔、沙笔(飞白)、毛(糙)笔、线(条)笔、点笔、染笔、渲笔、刚笔、柔笔、显笔、隐笔、皴笔、擦笔、秃笔。
以笔态(势)分为:正笔、侧笔、拖笔、卧笔、圈笔、勾笔、勒笔、抑笔、扬笔、顿笔、挫笔、点笔、拓笔。
以笔锋分为:中锋、侧锋、散锋、顺锋、逆锋、藏锋、露锋、回锋。
以笔意分为:笔情、笔趣、笔骨、笔气、笔格、笔意、笔调。
以水墨分为:干笔、湿笔、枯(燥)笔、渴笔。
以墨法分为:积墨、焦墨、泼墨、破墨、宿墨、彩墨。
以墨色分为:浓墨、淡墨、干墨、湿墨、亮(醒)墨、黑墨、老墨、嫩墨、沉墨、清墨、宿墨。
以墨阶分为:焦(枯)墨、浓墨、次浓墨、淡墨、次淡墨、最淡墨(淡若有无)。
(三)笔墨的宜忌
用笔宜劲、老、活、松、圆、厚、巧拙;用墨宜洁净。
笔墨忌描、涂、抹。
笔祛四病是板、刻、结、弱。
笔祛四端是牛头、鼠尾、蜂腰、鹤膝。
墨色三忌是浓墨忌痴钝,淡墨忌浮滑,浓淡相渗忌混浊。
三
无论古今,中国画家在绘画的实践中,多少都可能出现某些毛病和不足之处,历来的评论家都称之为“画忌”和“画病”。这对于那些初学者来说,可能是难免的。而前人对“病、忌”的认识是站在高山之颠的一种召唤。谁能做到,谁就可以到达顶峰。这正是对中国画家的全面要求,要求在实践中要刻苦勤奋,多走、多看、多思以外,还要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思想品德修养。以发挥所长,避免其短。
古人、前人历来认为,画有四病:即邪、甜、俗、赖。
“邪”是用笔不正(确)。
“甜”是画无内在美。
“俗”是意境平凡,格调不高。古人云:“宁作不通,勿作庸庸,板俗之病,甚于狂诞”。
“赖”是泥古不化,专事模仿。
饶自然曾经指出山水画应该注意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二曰远近不分,三曰山无气脉,四曰水无源流,五曰境无夷险,六曰路无出入,七曰石只一面,八曰树少四枝,九曰人物伛偻,十曰楼阁错杂,十一曰滃淡失宜,十二曰点染无法。这“山水十二忌”多是针对经营位置、构图布局的僻病而说的,技巧性要求多,而理性综合不够,注意了十二忌,可能画出一张好画来,但是它不可能成为评价山水画优劣的种种标准。黄宾虹曾把作画的“宜、忌”归纳为如下二十八字。“作画最忌者:死、板、刻、浊、薄、小、流、轻、浮、甜、滑、飘、柔、艳。应该做到:重、大、高、厚、实、浑、润、老、拙、活、清、秀、和、雄”。应该说黄宾虹所指作画的“宜、忌”是最高的艺术标准,它既是针对技巧性而言的,也是对创作过程而说的;既是对画作整体效果的要求,也是对画家修养意念的要求。不论山水、人物、花鸟画家,能做到黄宾虹指出的标准,则大家成矣。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