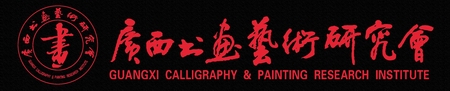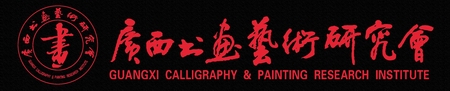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张波 何明
一
古希腊的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人啊,认识你自己吧。”“认识自己”是人生的重大课题。千百年来,人们对自己周围的世界,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透彻,唯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不大令人满意。“人”是什么?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课题,人体对于我们来说更是一个神秘的“谜”。
近日读画家吴冠中的画论,不禁眼界大开,读到《造型艺术离不开对人体的研究》文中的高论,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对于英国的雕刻家亨利?摩尔的作品,吴冠中说:“有人说他的灵感来自东方,他从我们的假山石里获得了重大的启示。我却反过来思考,那么我们的假山石又从哪里得来的启示呢?是从人体得来的。”这实在是使我大吃一惊。人体与假山石,在我们的视野里,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吴冠中接着说:“尽管设计假山石的艺人巧匠没有写生过人体,假山石的结构美是抽象的,但其起、伏、挑、擢的抽象美,并非是文艺之神阿波罗的恩赐,其实只是人们蹲、卧、前扑与回顾等生理活动的潜在的转化。”从心里说,如果是一般的艺术家发此议论,我是会报以讥讽的一笑的,但他是吴冠中,艺术成就和绘画理论摆在那里,我就不能不认真思考了。
吴冠中启发我们说,即使假山石与人体这种关系是被深深地隐藏着的,但在罗丹、摩尔这些有着长期丰富造型实践的艺术家看来却是一目了然的。假山谋处多一块石头或少一块石头,也许对别人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但在大师们的眼中那却是生命攸关人的脑袋问题!书法也是一样,一撇一捺,骑稳了没有?跨够了没有?或求严谨,或爱奔放,这些不同感情的体现依据的是人体的既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这是从艺术角度对人体的深刻的认识。
那么,画家们的山水画又如何呢?是不是也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去读画册,其实是去进行一次踏山勘水的旅行。
二
五代荆浩的《匡庐图》曾经使我激动不已,但当我读到他的学生李成的《晴峦萧寺》时,这种激动便变得理智起来。《匡庐图》的山,像一位依在床边酣睡的少女,令人看不厌,读不够,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而《晴峦萧寺图》,则是一位风韵绰约的少妇,给人一种甜美、成熟的气息,读着它,你会感到你正在和你的好友在交谈,她会告诉你很多令人高兴的信息,使你不得不静下心来想一些问题,或是提一些问题。
在五代自成一家的山水画家关仝,和荆浩并称“荆关”,也是李成的老师。他的《关山行旅》给我的感觉则是多方面的。面对画作,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使人禁不住要“哎哟”一声。画家笔简气壮,所画的山,石体坚凝,山峰峭拔,使人感到刚强与力量。但山峰上杂木丰茂,有枝无干,又给人一种柔韧有余的感觉。你会发现画家不仅仅是把一个具体的“人”推到你的面前,而是向你显示一种气质,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气质。
宋代画家范宽的《蹊山行旅图》,是一位蕴藏着诗情和力量的巨人,抱着双肩,屹立在你的面前,阻挡着你前行的去路,迫使你不得不抬头仰望,顿感自我的渺小,造化之浩大与神奇。细看,你便发现,山石是那么坚硬,犹如巨人的骨骼,给人美和力的无限想象。树的形象千姿百态,在向空间伸展的时候,仿佛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因而被强行扭曲,显示给人们的是一种力与力之间的抗衡。流水字高山飞流直下,但又不是直冲画外,使人猝不及防。飞瀑下面有一深潭,使人仿佛听到瀑布冲下深潭发出的闷雷般的响声,作品顿时有声有色。丛林中偶露的宫阙的一角,把人一下子拉回到凡间,使你在人间与仙境间反复遨游,反复玩味,便感大自然的无限,生命的无限。
关仝、李成和范宽,是五代到北宋时期的三大画派,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尽管三大画派风格各异,自成一家,但他们的作品都赋予了人格的魅力,使读者在读画的过程中,眼前时常闪现出人体美的影子。正如吴冠中先生说的,画家所画的山水,与人体的关系是被画家深深地隐藏着的,但画家在经营山石的位置时,平远、深远和高远的处理,就时不时有人体美在闪光。
审美学告诉我们,画家在写生(或称师造化)的时候,是在以个人审美的角度去描绘眼前的世界,他们对客观现实的写生时,是带着自己的审美观念的,画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眼前的景象。当他们进入创作的时候,更是按自己的意念直抒胸臆了。他们往往会使自己的想象和思考,融入自己所营造的意境里。这是一个主观的世界,客观世界会在这里消融,从而产生出意境化的作品。因此,画家创作出来的山水,就不能与客观世界的山水完全等同,它就隐藏着一种人体美的启示。我读过黄宾虹大师的《象鼻山》,作品中的象鼻山与客观世界的象鼻山,相去不下千里;我读过李可染大师的《雨中漓江》,画家的想象和思考营造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是很难找得到的。因此,有人说,依据想象创作的作品,才是一种境界化的作品,才能帮助我们找到最真实的、最接近真理的本质状态。
三
在中国有“画如其人”的说法,这大概就是由于画家那个“主观世界”延伸出来的。由于营造的是画家的主观世界,因此,作品就直接受到画家本人的影响,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画家,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关人品与画品的论述,前人之述备矣。我读过明代画家徐渭的画作《葡萄》,感觉上有点特别,但一时又说不出来。但细心读题与画上的诗作,新不禁戚然。诗曰: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联系到他多舛的命运和不幸的身世,始理解他的悲愤与无奈。“半生落魄已成翁”,是多么悲凉的呼号和叹息。因此,他所营造的主观世界,便给人一种悲且愤的感觉。
朱耷是明朝王室的后裔,对清朝取代明朝,他不甘、不服、不满。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格格不入,他都不屑一顾。对于他来说,打好的江山已经沉沦,鸟语花香已经不再。他恨这山这水,这花这鸟,一切的一切他都丢以白眼,只能苦笑不得。因此,他画的都是枯枝残叶、怪石瘦水,就是出现的鸟儿,对现实世界也是侧目相看。他的悲剧性的感悟,比徐渭显得更加寥阔和深沉,作品也就更具鲜明的个性,他在作品中所营造的主观世界,使人过目不忘,像钢凿刻石一样,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里。
如果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的主观世界更是千姿百态,七彩纷呈。对于同一个客观世界,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不同的反映。也就是说,客观世界只有一个,而主观世界则有千千万万。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代王室的后裔,面对明朝已经失落了的一切,他的反映与朱耷就大大的不一样。朱耷与现实格格不入,而他却与现实融为一体。在与大自然的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使深埋心中的悲剧意识逐渐得到冲淡,最后走向消失。对大自然的倾心和热烈追求,使原济用画笔营造的主观世界苍茫奔放,沉郁奇险,逼仄辽阔,稳重躁动,成为了当时的一面旗帜,与当时正统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对后来的“扬州八怪”产生极大的影响。
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友人踏着迷濛的细雨到我家造访,不为别的,只为向我推荐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画册——《李可染艺术丛书 山与水》。那是一本64开的小册子,里面收集了李可染的不少佳作。读后的第一个印象是“黑”。李可染山水画的用墨淋漓尽致,巨大的石山,充塞着画面,这种构图本身就容易给人一种逼仄之感,但画家却举重若轻,不但不惊慌,而且还大胆用墨,让画面黑到几乎没有一点透气的地方。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大面积的黑并没有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更没有使人产生黑暗,相反,倒使人感到一种眩目的明亮,一种放纵的轻松。这就是李可染营造的主观世界。
李可染的大胆探索,使他的山水作品独树一帜,不用看题款,只看画面就知道是他的作品,使“画如其人”这四个字得到了更有说服力的佐证。
四
由人体美谈到了人品美,似乎走得太远了。人是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上的,用人的目光来看世界,赤条条的人自然就是最美的。不言而喻,造型艺术要钻研人体美是天经地义的。我说的造型艺术,不单指绘画、雕塑,它包括工业造型建筑设计等等。其实说到底,世间的各行各业都是与人有关的。艺术家的吴冠中先生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研究人体美的,商业家的李冠中先生是从商业的角度去研究人的需求的,体育家、音乐家、教育家等等的X冠中先生都会带着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去研究人的。人发现创造了美,而大自然的美永远是人们创造美表现美的源泉,有了人才有美术一词。
高尔基说:“人才是至高无尚的,人是整个世界——复杂的、有趣的、深刻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一个永远也研究不透的课题。
★《造型艺术离不开对人体的研究》(见《吴冠中文集·艺术散论》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年12月)
返回目录